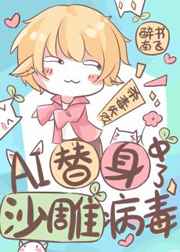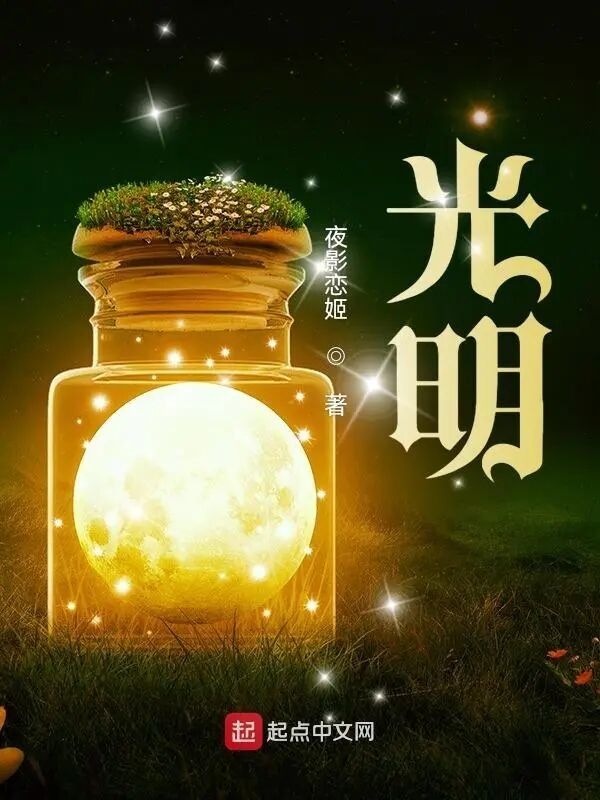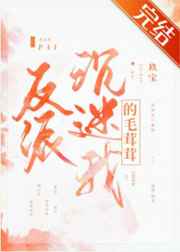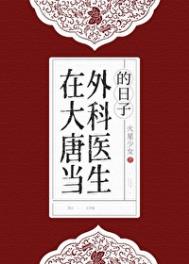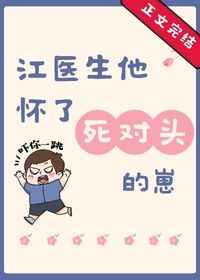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 作者钱穆(3/3)
、工部。
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户部)刑工,唐太宗是改为吏礼民(户)兵刑工,至宋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户)工礼,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其次序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次序遂为以后所沿袭。
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官吏必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
五品以上官,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
五品以下官,宰相不过问,全由吏部依法任用。
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吏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主管建设,各有职掌。
若以之比拟汉代之九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汉代九卿如光禄勋,就官名本义论,等于是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
唐代正名为吏部,掌管人事,名称恰当。
又如汉代掌军事的为“卫尉”,卫仍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
太常卿就名义言,也偏在皇家私的祭祀,唐代改为礼部,便确定为政务官了。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庞大。
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
由左右仆射分领。
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
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为吏部司是。
其余各司各有名称。
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
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
无此等衔者,则专在本省办公。
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一书,即因记载此尚书省中六部之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名。
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之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
此书遂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之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
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
此后中央政府之变动,只在中书门下发命令的部分,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省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此《唐六典》一书,系唐玄宗时,大体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纂辑,可说是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与本之理想和希望者不同。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亦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
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
其最堪重视者,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
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之一层。
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大体上看,而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
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
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
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
但我们谈《唐六典》的,仍不应仅当它是一部历史书,为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看。
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已在此书中大部具体化制度化了。
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
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
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也决无是处。
戊、唐代地方政府 以上讲的唐代中央政府,现在继续讲地方政府。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
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
唐玄宗时,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
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
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余。
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六千户以下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三千户以下为下县。
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
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
可见唐代的县比汉县为小。
唐代的州也分上中下三级,十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
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
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之掾属。
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
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
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不得不希望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
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
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亦灵活。
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就请地位相埒。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
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
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
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
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这已在汉制中说到。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
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异之点。
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此即所谓“分巡”“分察”。
监察中央的谓之“分察”,监察地方的谓之“分巡”。
中央方面最要者为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中书门下两省不在监察之列。
唐德宗时,尚书六部,吏礼兵工户刑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谓之分察。
分巡则分全国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
在汉制,此事规定六条视察,大体范围,不得越出于六条之外。
在唐代,名义上仍是巡察使,观察使,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各地区活动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川停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
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其地位自较原置地方官为高。
姑设一浅譬,如今制,教育部派督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此督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
彼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
但唐代则不然。
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是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
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
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
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
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
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
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为“藩镇”。
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
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有蹈其覆辙。
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
而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
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
而结果反而有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
这与后来清代的情形也相仿佛。
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就如现在的省主席。
清代的总督巡抚,就名义论,应该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的。
但结果长期驻扎地方,其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训致中央集权,地方无权。
而到后此辈巡抚总督,却不受中央节制,中央也便解体了。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内外政权分合一大条例。
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
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
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
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
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上会我们曾讲过汉代的选举制,到唐代,此项制度,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远在战国晚年,已有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提倡选贤与能,在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规定一项政府用人之客观标准。
汉代选举制度即由此提倡而来。
唐代的选举,其实还是由汉代的选举制演变,而我们此刻则称之为考试制。
汉代是乡举里选之后,而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的。
其先是对策,对策只是征询意见而已。
直要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才始正式有考试。
其时则考试只为选举制度中之一节目。
迨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自亦无从推行。
于是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
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
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
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
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
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皆可入登记表。
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
所以主持这项工作的便称九品中正。
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陟。
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比较有一客观标准。
而此项标准,则依然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依然仍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之遗意。
所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仍然是一丛众,一从贤。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
此是一理论。
至于贤人而实不贤,中中而并不中正,则另是一事实。
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标准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
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有关系的。
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
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
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以迄于南北朝,对于陈群此制,都继续采用,不能加以更新,这样毛病就出了。
首先是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
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
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
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
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这是第一点。
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未做官人通体要评,而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此本官之上司。
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混淆了。
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
在陈群时,为什么要大中正定由中央大官兼职呢?此因当时地方与中央已失却联系,故只就中央官来兼任大中正,好由他推选他的本乡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备供中央之任用。
但又为何中正簿上定要连做官人一并登记品评呢?因为如此做法,便可把当时已经滥用不称职的一批人澄清除去。
这些都是陈群创设此制时之苦心。
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算是坏制度。
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终于出了大毛病。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
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
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
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
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
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
而我们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
若肯接受以往历史教训,这一风气是应该警惕排除的。
在曹操当时,采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但此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丛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乙、唐代之科举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
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
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
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
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
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
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
现在自由报考之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
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
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
此外则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
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
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
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
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
又因吏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
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
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
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
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
谓政府用人,何不能民主投票方式。
其实西方近代的选举投票,亦何尝没有毛病。
而且我们把现行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
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
这亦何尝无毛病呢?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
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
故唐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即是财政与经济),此为选举。
其实在汉为选举,在唐即为考试。
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上,考试和选举是有同样的用意和同样的功能的。
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种政党政治,政务官大体在同党中选用,事务官则不分党别,另经考试。
此项官吏,可以不因政务官之更换而失去其服务之保障。
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
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
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
苟其勿自越出于此种习惯法之外,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在咨询众意。
这也不能说它完全无是处。
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
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
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
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
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
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
故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
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
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
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
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
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
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
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
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
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
读书人成为政脂肪。
若在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庸调制 现在再讲唐代的经济制度,主要的仍先讲田赋。
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租”“庸”“调”。
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
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
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以来。
均田制所与古代的井田制不同者,井田乃分属于封建贵族,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
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
说到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
“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
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
“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
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中国既是一个农业国家,人民经济,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
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
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
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
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
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这是唐制较胜于汉制之所在。
乙、唐代帐籍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即从北魏均田制算起,时期维持得并不久,而且推行也并不彻底。
因为北朝乃及初唐,全国各地,都是大门第豪族分布,而他们则依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
即使是不彻底的均田制度,也并不能长久持续。
推行了一时期,便完全破坏了。
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
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
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
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全国户口按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
此项户口册,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
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
帐则是壮丁册子,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
唐制每岁一造帐,三岁一造籍。
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则三年重造一次。
一次称一比,引起可以用来和上期的簿帐相比对。
唐制,州县经常须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政府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到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
这一工作相当麻烦。
户口有异动,田亩有还授(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
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
况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是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
某一家的年老者已逾六十,他的名字没有销去,小孩子长大了,没有添列新丁。
新授了田的,还是顶补旧人的名字。
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
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
恐怕并不要到达户口太多,田亩太少,田地不够分配,而租庸调制早得崩溃了。
这是一种人事的松懈。
至于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扰此项制度之进展,那更不用说了。
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
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再说此项制度,其用意颇近似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
这要全国民众,每个家庭,每个壮丁都照顾到,计划到。
在近代大规模地利用科学统计,交通方便,声息灵活,印刷术容易,尚且感到有困难。
古代交通既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亦贵,书写不便,这些都是大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户口登记逐渐错乱,此制即无法推行。
迫不得已,才又改成两税制。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丙、唐代的两税制 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
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
因此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
此制与租庸调制之不同,最显著者,据唐时人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
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
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
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
如是则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
这不能不说是此制之好处。
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
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这一制度和古制相较,也有它的毛病。
据当时一般意见说,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清楚,现在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
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
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而更重要的,则在此一制度规定租额的一面。
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直从井田制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
如汉制规定三十税一,唐制则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这在全国各地,一律平等,无不皆然。
但两税制便把这一传统,即全国各地田租照同一规定数额征收的那一项精神废弃了。
在旧制,先规定了田租定额,然后政府照额征收,再把次项收来的田租作为政府每年开支的财政来源,这可说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
但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像是量出为入的。
因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即唐代宗之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
如是一来,在政府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但相因而起的弊病却大了。
因为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
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
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
其他州县,大约相似。
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
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
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政府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交各地方政府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
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
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
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
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
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
虽说此后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著的事实呀!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
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
让我再举一实例。
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
纳税之时,多配绫绢。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
往输其一,今过于二。
又据四十年后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
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
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
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
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
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
最主要的是,则是政府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
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
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
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
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
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
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
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
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
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现在再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两两相比,又见有恰恰相反之势。
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
其下层贫穷,政府却并未注意到。
总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穷人还是很多,甚至于逼得出卖为奴。
政府的轻徭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
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
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
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
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
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
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
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
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
汉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只注意不让你过富,而没有法子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之陷入于过穷。
不过这也仅是说汉唐两代关于经济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仅限于初唐。
待后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茶盐各项也都一一收税,便和汉代差不多。
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色令智昏刘水水
- 这甜宠给你要不要啊[快穿]岁砚
- 红男绿女常书欣
- 反派老攻为我变绿茶了雨落轻尘
- 咸鱼女配在恋综躺平后爆红阿堃
- 我的人生模拟器凿砚
- 咸鱼摆烂复婚综艺[娱乐圈]塬
- 我在东京教剑道范马加藤惠
- 剑啸灵霄流浪的蛤蟆
- 关小姐又在写情书茴笙
- 我转生成了横滨碰瓷王筱潋
- 掩盖武和平
- 我在古代当先生北沐南
- 大院二婚妻[八零]青雨梧桐
- 阴阳鬼术巫九
- 九阳神王寂小贼
- 桃花折江山白鹭成双
- 和豪门大佬隐婚后林多多
- 身为女王如何拒绝爱意吾九殿
- 抽卡无涯,日赚十亿江山沧澜
- 醒日是归时含胭
- 死遁前向男二倾情表白夜饮三大白
- 新来的转学生强到炸裂晚秋初十
- 强取豪夺,人夺错了枭钥
- 我在女团艰难求生[穿书]兔子蛋糕
- 攻略女帝师尊,这逆徒我当定了!影十三
- 纯阳贱神三哥妄语
- 什么,狼人杀也能加国运水云寒
- 天路神影黎明光
- 叩问三十三重天的逆命者望川欲成山
- 从高武开始修仙:我的系统能加点藏情空
- 诸子封天录我家有团
- 耕耘问道路秋三晨
- 诸天通灵:从玄元界杀到无敌用户19910905
- 红楼大当家潭子
- 为何寡人会怀孕!长生千叶
- 南洋往事康塞日记
- 男友用我照片网恋之后小兰书
- 财迷少女暴富记可可酒
- 求求了,让我安静地当个炮灰!芳媛
- 灵气有毒:母巢启示录轩墨试笔
- 医身玄道归藏蓬
- 林渊墨海书魂娱乐枭雄
- 仙子,你怎么有条蛇尾巴打个长工
- 修仙:我的飞剑有点多不想做封面的小透明
- 她不想高调,奈何酸意爆表芳媛
- 重生之我成了一条蛇心想是蔯
- 仙妻从天而降关心你的猪呀
- 玄幻:师尊师尊,徒儿还要贴贴别离雨
- 灵徵未兆不如睡
- 煞破天穹纪秋烨
- 剑灭诸天之起源黄院长
- 修仙内卷时代流离火
- 重生:我躺平退宗了,怎么你们又后悔了爱笑的毛毛虫
- 陆惊宴盛羡陆惊宴盛羡
- 绝品上门女婿苏阳叶芷涵
- 镇压仙女门三年,出世即无敌古都第一白
- 攻略精灵(西幻万人迷NP)珀长烽(请监督我写文)
- 猫总会被蝴蝶吸引引路星
- 春风眷我周镜
- 我百年成帝,直接震麻了黑暗至尊猫也爱华夏
- 彼岸的星门月下的男孩
- 异能大佬不需要晶核沈冗
- 洪荒快递指南:我在末法时代开盲凌尘决
- 退下,让朕来油爆香菇
- 太古凶煞:王者归来爱吃玉米的中年大叔
- 救世从召唤玩家开始织吖
- 抢救修仙者之旅吟诵田园
- 纯阳贱神三哥妄语
- 无上战祖狂鲨
- 替姐姐嫁入宅门的第四年一枝嫩柳
- 和糙汉邻家哥哥恋爱了迪克羊仔
- 老夫七十岁,正是宠妻的好年纪枫卷残云
- 重生之我成了一条蛇心想是蔯
- 异界仙途之建世传奇大漠三友
- 山海烛龙房三善
- 太上噬仙诀白龙城主
- DNF之召唤师今天也想躺平小白不不不白
- 策划到底给了我什么人设[西幻]冥河摆渡者
- 我家武馆连龙珠火吧,胜利的小李
- 支配神话轻若君子
- 九转极道斩苍穹snxobukn
- 垂钓万界废材逆袭成团宠茜影随形
- 长生皇子:开局无敌,看王朝起落唱书人
- 精灵小姐和人鱼公主灯影诗人
- 仙祭传云水山客1
- 龙家传【1】天为吾名
- 开局退婚女帝,奖励混沌圣体!夏夏的虾
- 我百年成帝,直接震麻了黑暗至尊猫也爱华夏
- 瑕疵品东吴一点红
- 被仙子榨干后,我觉醒无敌系统多冷的隆冬
- 掌门,老夫来助你修行雨夜终曲
- 收徒成功后,我开始起飞建木大叔
- 无上战祖狂鲨
- 热岛张佩奇
- 天路神影黎明光
- 耕耘问道路秋三晨
- 不入爱河蒋牧童
- 南洋往事康塞日记
- 神级熊孩子系统点化万物变随从石仙镇